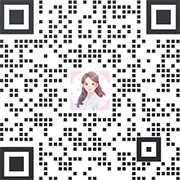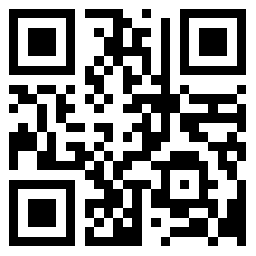深部脑刺激治疗病人持续植物状态
发表时间:2009-12-07 浏览次数:1131次
作者:朱宏伟 综述 李勇杰 审校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 北京功能神经外科研究所, 北京 100053
【摘要】深部脑刺激是一种治疗持续植物状态的较新技术,在各种保守治疗不能促醒的基础上,及在病人家属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深部脑刺激可作为一种尝试性且有一定前途的治疗方法。近年来,该技术在术前检查、手术方法、术后调试和疗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本文对此进行综述。
【关键词】 深部脑刺激 持续植物人状态 微意识状态
伴随着重症医学的进步,在成功救治许多颅脑病变危重病人的同时,也增加了许多较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的幸存者,其中约30%~40%病人的转归结果是持续植物状态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PVS)。1972年,Jennett等[1]第1次提出PVS的概念,认为PVS是一种严重脑损害后的状态,病人由昏迷状态转入没有可察觉意识的觉醒状态。PVS可以用PVS量表 (Society for Treatment of Coma,Japan,1997) 进行评估。近年来发现,PVC可能通过深部脑刺激 (DBS) 获得苏醒,本文对此综述如下。
1 DBS治疗PVC的提出与概况
1994年,The Multi-Society Task Force of PVC专家组总结了PVS的医学特点:PVS是一种完全不能感知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临床状态;有睡眠觉醒周期;完全或部分保留了脑干和下丘脑的自主功能;PVS病人对视觉、听觉、触觉或有害刺激无持续的、可重现的、有目的或随意的行为反应;不能进行语言理解或表达;大小便失禁;有残留且多变的脑神经或脊髓反射;脑损害1个月以上。据文献报告,外伤后PVS病人12个月后不可能苏醒,而非外伤性PVS 3个月后苏醒罕见;但临床实践中也不乏个例发生。尽管一些病人临床症状符合PVS的标准,但临床严重程度的分级不同,评分不同,电生理指标不同,预后也有明显的差别。如何准确判断是否是PVS以及PVS的评分,对客观判断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十分重要。
即使是符合上述PVS临床特点的病人,脑损害程度差别也很大,这种损害包括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PVS病人绝大多数不能自然从植物状态恢复,但选择合适的病例,通过恰当的治疗,部分病例有望从植物状态苏醒。
Yamamoto等[2]按照上述标准,选择各种脑损害导致的PVS病人21例,病程在3个月以上,进行神经功能和电生理评估,然后植入DBS刺激系统进行刺激,随访10年,分析其治疗效果和长期生存率。该组病人年龄19~75岁;昏迷原因如下:脑外伤9例,脑血管意外9例,缺血、缺氧性脑病3例;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采用立体定向的方法,靶点选择中脑网状结构的楔状核 (nucleus cuneiformis) 2例,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 (centre median-parafascicular complex) 19例;刺激方式为白天1次/2~3 h,每次刺激30 min,刺激频率固定在25 Hz。结果病人苏醒8例 (38.1%),其中1年内苏醒7例,最早于刺激5个月时苏醒。从苏醒病人的受伤原因来分析,均为脑外伤或脑血管意外所致,而3例缺血、缺氧性脑病病人均无苏醒。总结这8例病人的特点如下:具有长潜伏期的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ABR) Ⅴ波和体感诱发电位 (SEP) N20,连续EEG频率分析显示去同步化或轻微去同步化模式,能够记录到疼痛相关的P250且振幅超过7 μV。尽管这些病人也有自己苏醒的可能性,但DBS能够加速恢复过程,改善预后。
Cohadon等[3]报告了25例PVS的治疗效果,均选择外伤后3个月仍不能苏醒的病人,靶点选择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刺激时间从早8点到晚8点,其中13例于刺激1~3周后有明确的效果,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意识和反应能力的恢复;所有病人随访1~12年,均仍严重残废,死亡2例。
DBS刺激上述靶点可以产生强大的唤醒作用,并在代谢方面表现为局部脑血流量 (r-CBF) 和局部脑组织氧代谢率 (r-CMRO2) 增高。刺激中脑网状结构可引起脑电图的去同步化。与脑干的损害程度相比,PVS病人大脑皮质功能的损害更严重。脑干和大脑皮质的联系对维持意识非常重要。选择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作为治疗靶点的依据在于,低频刺激该核团能够诱发EEG的募集增加 (incremental recruiting) 和反应增强 (augmenting response),高频刺激能够诱发EEG的去同步化。而刺激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可诱导EEG的调幅现象。
微意识状态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MCS) 与PVS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预后差别很大,需要仔细鉴别。微意识状态的特征是:具有间断但可明确辨别的有意识行为,与昏迷和PVS的区别在于存在特有的行为特征。MCS经常是暂时的,但也可长期存在。Yamamoto[4]报告了5例MCS的DBS治疗效果,均在伤后3个月进行评估,刺激靶点选择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其中4例从卧床恢复到能下地行走,生活质量有明显进步。由此可见,MCS的治疗效果远优于PVS,故诊断方面要注意鉴别,避免把MCS误诊为PVS,错误地得出经短期治疗将“植物人”成功复苏的结论。
除此之外,尚有右正中神经刺激 (RMNS) 治疗昏迷的报告,正中神经可以理解为与外伤后昏迷的脑相互作用的一扇“门”,周围神经刺激产生中枢神经系统效应,经2~3周的刺激,可以通过增加多巴胺的水平而加速急性脑损伤后的苏醒过程。RMNS的效应已经得到神经电生理、神经影像和脑脊液相关代谢物质检查的证实,是一种低廉而微创的治疗方法[5]。
2 适应证
一般认为,DBS治疗PVS的适应证如下:①各种保守治疗方法促醒失败的病人,一般情况良好,能够耐受麻醉和手术。②昏迷3~6个月为相对适应证,昏迷时间越长,苏醒的机会越少。③神经影像检查显示至少一侧半球相对完整,脑干结构无严重损害。④脑功能状态检查显示皮质的代谢正常或减低,但脑干的代谢基本正常。⑤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ABR)Ⅴ波正常或延长,ABR电位消失的病人不宜手术。⑥SEP检查显示N20 (反应丘脑皮质传导通路的功能) 潜伏期延长。⑦连续EEG频率分析 (continuous EEG frequency analysis;用于分析反应脑干和大脑皮质之间的功能联系) 为去同步化或轻微去同步化模式。
3 术前检查
3.1 神经影像检查 近期头颅CT、MRI (T1、T2、Flair相),了解脑组织 (尤其是海马) 在结构上的损害情况。脑功能状态检查包括fMRI、脑SPECT (脑灌注和脑血流、r-CBF、r-CMRO2及脑糖代谢率) 和脑PET检查,以了解脑的功能状态。
3.2 脑脊液化验 了解刺激前后脑脊液内神经递质及其代谢产物的变化。
3.3 昏迷评分 评分量表很多,比较常用的是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lasgow Coma Scale,GCS) 和PVS量表评分 (表1)[6]GCS的优点是简单普及,缺点是灵敏度较差,对临界状态的意识变化难以准确反映。PVS量表评分项目较多,能比较客观地反应PVS治疗前后的变化;且项目内容较为具体,能够准确界定,不同评估者进行评估的差别较小。
3.4 术前神经生理学检查 是术前评估的重要内容,为决定是否进行刺激手术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ABR、SEP、疼痛相关电位P250和持续脑电图频率分析 。ABR的记录结果分为三种类型:①无反应;②Ⅴ波的潜伏期延长,即Ⅰ~Ⅴ间期超过正常值2个标准差以上;③正常。SEP结果分为三个类型:①无N20;②N20延长,即N20的潜伏期超过正常值2个标准差以上;③N20正常。Tomota等[7]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昏迷病人若短潜伏期的SEP (包括P13、P14、N18和N20) 缺失或波幅降低,提示预后不良。PVS病人大脑活动的特征可通过疼痛刺激诱发的大脑晚期正成分 (late positive component) P250来反应,P250是惟一能够直接量化疼痛刺激的皮质反应,且不包括运动系统功能的指标。P250主要用来判断有无脊髓丘脑束的功能障碍,其记录结果分为三种类型:①无P250;②P250振幅在7 μV以下;③P250振幅7 μV以上。持续脑电图频率分析分为三种类型:①无去同步化模式 (no desynchronization patten):峰频率 (peak frequency) 的改变只出现在α和其他更低的频率范围,高频率段无峰频率的改变。②轻微去同步化模式 (slight desynchronization patten):去同步化存在,但持续时间短暂,占总时间的10%以下,高频范围的功率较低。③去同步化模式 (desynchronization patten):是一种低振幅、高频率的改变形式;此形式经常出现,去同步化时高频范围功率的增长十分明显。
4 手术方法
手术步骤如下:静脉麻醉下将立体定向仪头架固定在病人的颅骨上。行MRI扫描后,在工作站上进行层厚2~3 mm的矢状及水平重建。
4.1 解剖定位 脑内深部结构与前后联合线 (AC-PC线) 关系固定,与性别、年龄、种族等无明显差别。通过标准脑图谱确定与AC-PC线的相对关系,我们可以对影像上不能直接看到的脑深部核团进行定位,然后将其投射到脑立体定向仪的三维坐标上,即完成解剖定位。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位于前后联合线平面,横坐标 (x) 为5 mm,纵坐标 (y) 为后联合前7 mm。
4.2 功能定位 由于体位变化、脑脊液流出后的脑移位以及个体解剖差异等原因,术中应进行微电极记录和刺激,进一步明确与脑内重要结构的关系,以确保刺激电极准确植入到靶点。
4.3 植入DBS系统 DBS系统由1个发生器、2根颅内刺激电极和连接线组成,发生器植入部位在右锁骨下胸大肌表面,2根颅内刺激电极分别植入到双侧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通过皮下隧道用连接线把发生器和颅内刺激电极连接起来。术后需复查MRI,验证刺激电极是否准确达到中央中核束旁复合体。
4.4 术后程控 该系统最大的优点是术后可体外进行程控,进行不同刺激参数、刺激模式和刺激点的变更,并可依据电生理指标的变化进行参数调整。
其他核团的植入方法与此相似[8]。
5 术后调试和疗效评估
刺激参数调整主要包括刺激频率、刺激强度和波宽的调整。一般认为,刺激频率选择25~40 Hz比较合适,因为高频刺激产生的是抑制效应,低频刺激产生的则是兴奋效应。如前所述,刺激强度依据每例病人的反应而定,一般选择略高于刺激诱发觉醒反应的阈值。波宽可使用90~120 μs,以逐渐增加为妥。除上述参数外,尚有刺激模式和刺激位点的变化,刺激模式分两种:①间断刺激,每2 h为1个周期,每次刺激30 min,刺激“开”状态0.5 h,“关”状态1.5 h,交替进行。②刺激时间从早8点到晚8点,晚上不刺激,模拟觉醒睡眠周期。建议开始时使用模式①刺激,一段时间后改为模式②。每1根颅内刺激电极有4个刺激位点,根据病情变化情况可以进行调整。
术后每月进行PVS量表评分,必要时进行相关的电生理检查,依据PVS量表评分进步的程度进行刺激参数调整。调整间隔不能少于1个月,频繁变更刺激参数对治疗不利,且难以评估刺激效果[9]。
DBS治疗PVS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关于其长期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且适应证和刺激靶点选择尚无定论。总之,在各种保守治疗不能促醒的基础上,及病人家属知情同意的前提下,DBS可作为一种尝试性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1] JENNETT B, PLUM F.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after brain damage. A syndrome in search of a name [J]. Lancet, 1972, 1(7753): 734-737.
[2] YAMAMOTO T, KATAYAMA Y, KOBAYASHI K, et al. DBS therapy for a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ten years fol- low-up results [J]. Acta Neurochir, 2003, 87(Suppl): 15-18.
[3] COHADON F, RICHER E. Deep cerebral stim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vegetative state. 25 cases [J]. Neu- rochirurgie, 1993, 39(5): 281-292.
[4] YAMAMOTO T, KOBAYASHI K, KASAI M, et al. DBS therapy for the vegetative state and minimally conscious state [J]. Acta Neurochir, 2005, 93(Suppl): 101-104.
[5] COOPER E B, Cooper J B. Electrical treatment of coma via the median nerve [J]. Acta Neurochir, 2003, 87(Suppl): 7-10.
[6] NODA R, MAEDA Y, YOSHINO A. Therapeutic time win- dow for musicokinetic therapy in a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after severe brain damage [J]. Brain Inj, 2004, 18(5): 509-515.
[7] TOMOTA Y, FUKUDA C, MAEGAKI Y, et al. Reevalua- tion of short latency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 (P13, P14 and N18) for brainstem function in children who once suffered from deep coma [J]. Brain Dev, 2003, 25(5): 352- 356.
[8] MORITA I, KEITH M W, KANNO T. Dorsal column sti- mulation for 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 [J]. Acta Neurochir, 2007, 97(pt 1): 455-459.
[9] GLANNON W. Neurostimulation and the minimally cons- cious state [J]. Bioethics, 2008, 22(6): 337-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