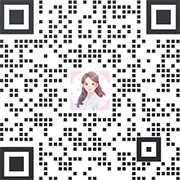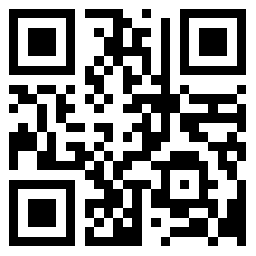外科感染的对策及胆道感染抗生素的合理应用
发表时间:2011-05-26 浏览次数:796次
作者:李奇为 季福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 200127)
【摘要】 外科感染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其中胆道感染所占比例较大。人类在控制外科感染方面虽已取得巨大进步,但病原菌的变迁、耐药性的增加使得外科感染越来越复杂,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严峻。因此我们需采取全方位对策,并合理使用抗生素。
【关键词】 外科感染·胆道感染·抗生素
1 外科感染病原菌不断变迁
20世纪60年代之前,外科感染的主要病原菌是革兰阳性球菌,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70年代起,革兰阴性杆菌开始逐渐增多,以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为代表,成为外科感染的主要致病菌。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大量敏感的革兰阴性菌被选择性杀灭,革兰阳性球菌又有了增加的趋势。中国细菌耐药检测研究结果显示:革兰阳性球菌所占比例在1999年为28.8%,2001年为33.5%,2003年为38.2%[1-2]。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多见,其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主要是表皮葡萄球菌)和肠球菌。在革兰阴性需氧杆菌中,大肠杆菌比例有所下降,但阴沟肠杆菌、产气杆菌、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等越来越常见。80年代厌氧菌参与的混合感染和真菌感染日益增多,此类感染多发于病情复杂、久治不愈、免疫力低下、长期使用抗生素的患者,病死率高[3]。随着厌氧菌培养、分离和鉴定技术的改进,厌氧菌的检出率大大提高。根据国内多个研究报告,目前外科感染常见菌种为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葡萄球菌,三者合计占病原菌总数的50%。其他较常见细菌是不动杆菌、肠杆菌属、肠球菌和克雷伯肺炎杆菌。总体上革兰阴性杆菌仍占优势,约60%~80%。革兰阳性球菌占30%~35%,另外还有3%~8%的真菌[4-6]。值得注意的是常见病原菌的耐药菌株增加迅速,如甲氧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beta-lactamase,ESBLs)的大肠杆菌或克雷伯肺炎杆菌[7-8],它们对多种抗生素交叉耐药,临床治疗困难,应引起重视。
2 病原菌的耐药性不断增加
滥用抗生素的直接后果是筛选出大量耐药菌株,引起难治性或继发性感染[9]。其对多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因时因地而异。黎沾良[6]研究发现,MRSA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istant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ulococcus,MRCNS)对全部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即使体外试验有一定敏感率,在体内均耐药。对其他绝大多数抗生素也有很强的耐药性,但对糖肽类抗生素(万古霉素、替考拉宁)仍十分敏感。但已有报道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10]。此外肠球菌也对多种抗生素耐药,更出现了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us,VRE),大大增加了防治的难度。
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出现了较多产ESBLs或AmpC酶的菌株。已有研究表明,ESBLs能抑制三代头孢菌素的抗菌能力,并可对非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产生交叉耐药[11]。非发酵菌包括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耐药情况都很严重。碳青霉烯类的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抗革兰阴性杆菌效果最好,但是仍有个别革兰阴性杆菌对其耐药。
3 外科感染的预防措施
外科感染中最常见的是外科切口部位感染(Surgical site infection,SSI),这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999年提出和发展的一种新概念,包括任何一种发生于手术部位的感染[12]。主要包括:1)浅表SSI,发生在切口皮肤和皮下组织;2)深层SSI,侵入肌肉和筋膜;3)器官/间隙SSI,如腹腔脓肿、脓胸、关节间隙感染。
SSI的发生取决于细菌的数量和毒力、局部环境、宿主全身抵抗力[13]。此外还与外科手术切口种类密切相关。根据手术切口被细菌污染的情况,美国国家院内感染评估中心(NNIS)将手术切口分为清洁、清洁-污染、污染和污秽4类,切口感染率从<2%依次升高至>10%。
外科感染的预防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手术部位皮肤准备,调整患者的血糖等,将患者抵抗力提高到最佳状态;二是手术操作要轻柔,减少损伤;三是加强围手术期处理,合理使用抗生素等。近年来,部分外科医生过分相信抗生素的作用,盲目地大量联合使用抗生素。在我国,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据文献报道,美国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约占30%,而我国高达67%~80%[14]。1997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我国一、二、三级医院住院患者抗生素的使用率分别为90%、80%和70%[1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如何合理应用抗生素防治外科感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4 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
预防性抗生素应短期使用以减少手术部位的细菌数量,提高患者预防感染的能力,建议只用在清洁-污染或污染手术,污秽手术则应治疗性使用抗生素。对于清洁手术是否使用预防性抗生素 ,目前还存在争议。清洁手术感染率<2%,一般认为清洁手术无需使用预防性抗生素[16],除非有以下明确指征:1)患者有感染高危因素,如高龄、营养不良、肥胖、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等。2)清洁大手术,一旦感染后果严重,如乳腺癌根治术、门脉高压的门体分流术、门奇断流术等。3)植入人工材料的手术,如人工关节置换术、心脏瓣膜置换术等[17]。4)术中手术野污染。5)手术时间>2 h。
预防性抗生素使用应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理想的预防性抗生素,应视预防目的而定。预防切口感染,应选用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生素;预防手术部位或全身感染,应依据手术野污染或可能的污染菌种选用。选用的抗生素必须是疗效肯定、安全、使用方便及价格低廉的药物。2)合理的给药时间是切口前0.5 h[18]。有研究表明在手术即将开始时使用抗生素,能使整个手术期间即发生细菌污染期间的血液和组织中维持有效的杀菌浓度,此时手术部位流出的血液和组织也有强大的杀菌活性,可收到最佳预防效果[19]。过早给药或术后给药,对患者有害无益。3)原则上使用单次剂量即可。如抗生素半衰期短、手术时间长,要在手术全程维持有效的血药浓度,可在术中加用1次。有报道手术时间、术中失血、输液等因素可影响血药浓度[20-21]。我国卫生部建议手术时间超过3h或失血量>1500 mL,可在手术中给予第2次。4)持续时间。术后是否继续使用抗生素,取决于术中发现腹腔感染的程度和术后发展趋势[22]。延长用药时间不会增加预防感染效果,相反会引起二重感染产生耐药菌株。有报道发现难辨梭状芽孢杆菌性肠炎与不恰当的使用抗生素有关[23]。美国外科感染协会建议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不应超过24 h[18]。我国卫生部也建议清洁手术预防用药应不超过24 h。清洁-污染手术预防用药时间也为24 h,必要时可延长至48 h。污染手术依据患者情况适当延长。污秽手术抗生素应按治疗性应用而定。但有时临床难以鉴别感染与炎症反应,为求稳妥,延长预防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是认识上的误区。只有证据明确的感染或发生感染将是灾难性的,才是继续使用抗生素的指征。
5 治疗性抗生素的使用
治疗性抗生素使用应有明确指征,临床上应有明确证据诊断为细菌性感染,积极采集标本送检,尽早查明感染源。选用何种抗生素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而定。在未获得药敏结果前,根据感染的性质和部位推断最可能的病原菌,进行经验性治疗,根据药敏结果过渡到针对性用药。能用窄谱抗生素就不随意使用广谱药物。
外科医师应掌握本地区本单位感染性疾病常见病原菌种类及耐药情况,对控制及预防感染的发生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对本地区本单位近期细菌谱及耐药性进行动态监测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还应掌握药物的药理作用特点,针对具体患者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抗生素疗程因感染不同而各有差异,一般用至体温正常及症状消退后72~96 h,特殊情况需较长疗程。
联合用药应有明确指征,单一药物可有效治疗的感染不必联合用药。除以下几种情况:1)病原菌未查明的严重感染,包括免疫缺陷者的严重感染。2)单一抗生素不能控制的需氧菌和厌氧菌混合感染,2种或2种以上病原菌感染。3)单一抗生素不能有效控制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或败血症等重症感染。4)需长程治疗,但病原菌易对某些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感染。5)联合用药选用协同或相加抗菌作用的药物。通常采用2种药物联合,3种以上仅使用于个别情况。
6 胆道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和耐药性
胆道感染是外科常见疾病,多由于进入胆道的细菌在结石、狭窄、外来压迫等机械性梗阻因素和伴随的充血、水肿、痉挛等因素刺激下异常繁殖而致的胆道炎症,严重时会导致多个器官功能受损,危及生命。
通常认为正常胆汁是无菌的,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时人体防御机制被削弱,在某些致病因素诱导下,菌群发生异位,转移到肝胆道产生致病作用。一般认为胆道感染细菌主要来源于肠道,经十二指肠乳头逆行感染的细菌最多[24],最常见的是革兰阴杆菌,以大肠杆菌和克雷伯杆菌为主,随着时间和地区的改变,细菌的种类有所变化。表现为:1)菌群种类增加,混合厌氧菌感染比例增加,革兰阳性球菌感染增多。Mukaiya等[25]分离109株胆道病原菌,其中革兰阴菌70株,革兰阳性菌27株,厌氧菌12株,最主要的致病菌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占75%。Waele等[26]报道最主要致病菌为大肠杆菌、肠球菌、链球菌。国内多篇报道也基本一致[27-28]。2)真菌感染增多。随着抗生素及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用,真菌感染有所上升。3)L型细菌引起关注。L型细菌是受某些条件影响而失去细胞壁的状态下,仍能继续繁殖的一类变异细菌的统称。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干扰了细菌细胞壁的合成,胆汁高盐能维持L型细菌长期存活、生长或繁殖,引起胆囊炎的反复发作。探究这些改变的原因,可能是盲目的大量使用抗生素导致敏感菌株被抑制或杀灭,耐药菌株大量滋生或繁殖,成为主要致病菌,这无疑增加了治疗胆道感染的难度。与此同时,伴随着细菌谱的改变,细菌的耐药性也明显增加,尤其是对青霉素及多种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产生了极高的耐药率。陈国忠等[28]报道胆汁中分离的致病菌对常用抗生素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尤以铜绿假单胞菌、肠球菌属、葡萄球菌属的多重交叉耐药严重。
7 胆道感染的抗生素应用
治疗胆道感染的抗生素应选用能在胆汁中形成较高浓度的种类,如氨苄西林、美洛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哌酮、头孢曲松及环丙沙星等。有报道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和头孢曲松在胆汁中的浓度可以达到血药浓度的10倍以上[29-31]。胆道内抗生素的浓度会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1)肝功能。肝功能异常的患者胆汁内抗生素浓度一般低于肝功能正常的患者。2)胆管有无梗阻。胆道梗阻时由于胆道内压力增高,抗生素在胆汁内的浓度会相应减少,严重时胆汁内几乎没有抗生素。3)给药途径。大多数抗生素注射较口服后胆汁浓度高。4)药物用量。
因胆道感染主要以革兰阴杆菌为主,临床上治疗胆道感染应选用针对革兰阴杆菌的抗生素。重度感染和复杂病例还需考虑覆盖绿脓杆菌和厌氧菌。感染早期,无需考虑肠球菌,当感染不易控制,反复培养出肠球菌,尤其血中出现肠球菌,应考虑肠球菌胆道感染可能。经验性用药应结合当地常见致病菌及其对抗生素耐药性等情况,选用能覆盖革兰阳性菌及革兰阴性菌,甚至是厌氧菌的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不同抗菌谱的药物。由于胆道患者常有胆道梗阻,胆管高压阻碍抗生素经胆汁排泄,因此适时的外科手术干预、胆道穿刺引流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此外注意患者全身情况,考虑到抗生素毒副作用,应酌情减量使用。抗生素使用效果应在72 h后评定,无特殊理由,不应频繁变动。在获得药敏结果后,若临床反应与实验室报告不符,应以临床为主。病情无好转或恶化,无论药敏结果如何,都应认真分析抗生素选药、配伍、剂量、用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 李家泰, 李耘, 齐慧敏. 2002-2003年中国革兰阴性细菌耐药性监测研究[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05, 28(1):19-29.
[2] 李家泰, 齐慧敏, 李耘. 2002-2003年中国医院和社区获得性感染革兰阳性细菌耐药监测研[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005, 28(3):254-265.
[3] 黎沾良. 抗感染治疗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03, 10(3):181-182.
[4] 唐培, 刘彤, 李金, 等. 2004-2006年医院外科感染常见细菌构成及耐药情况分析[J].天津医药, 2007, 35(8):584-586.
[5] 申正义, 王洪波, 孙自镛. 湖北地区外科感染常见致病菌1314株耐药性监测分析[J].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01, 16(4):231-233.
[6] 黎沾良. 外科感染常见病原菌及耐药现状[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7, 27(12):937-939.
[7] 陈亚红, 姚婉贞, 周庆涛, 等. 产ESBLs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变化[J].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07, 7(2):124-126.
[8] 刘兴态, 汪华, 曾蓉. 产ESBLs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的检测及耐药性分析[J].检验医学与临床, 2007, 4(3):182-183.
[9] Farber MS, Abrams JH. Antibiotics for the acute abdomen[J]. Surg Clin North Am, 1997, 77(6):1395-1417.
[10] 张婴元. 细菌耐药趋势与抗感染治疗的若干问题[J].中华医学杂志, 2001, 81(1):2-4.
[11] Meyer KS, Urban C, Eagan JA, et al. Nosocomial outbreak of Klebsiella infection resistant to late-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J]. Ann Intern Med, 1993, 119(5):353-358.
[12] Mangram AJ, Horan TC, Pearson ML, et al. Guideline for prevention of surgical site infections, 1999. Hospital infection control practices advisory committee[J].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 1999, 20(4):250-278; quiz 279-280.
[13] Odom-Forren J. Surgical-site infection: still a reality[J]. Nurs Manage, 2005, Suppl:16-20.
[14] 黎沾良. 我国外科感染的诊治进展[J].中华外科杂志, 1999, 37:589-591.
[15] 李继光, 李芳久, 何利. 综合性医院药品应用现状及药品过度使用的初步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 2002, 22(11):12-16.
[16] Minnema B, Vearncombe M, Augustin 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surgical-site infection following primary total knee arthroplasty[J]. Infect Control Hosp Epidemiol, 2004, 25(6):477-480.
[17] Page CP, Bohnen JM, Fletcher JR, et al. Anti microbial prophylaxis for surgical wounds.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care[J]. Arch Surg, 1993, 128(1):79-88.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R].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2004:3.
[19] 黎沾良. 外科感染防治: 一个永恒的话题[J].中华实验外科杂志, 1999, 16:483-484.
[20] Kaiser AB, Herrington JL Jr, Jacobs JK, et al. Cefoxitin versus erythromycin, neomycin, and cefazolin in colorectal operations. Importance of the duration of the surgical procedure[J]. Ann Surg, 1983, 198(4):525-530.
[21] Condon RE, Wittmann DH.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general surgery[J]. Curr Probl Surg, 1991, 28(12):801-949.
[22] Schein M, Assalia A, Bachus H. Minimal antibiotic therapy after emergency abdominal surgery: a prospective study[J]. Br J Surg, 1994, 81(7):989-991.
[23] Kreisel D, Savel TG, Silver AL, et al. Surgical antibiotic prophylaxis and clostridium difficile toxin positivity[J]. Arch Surg, 1995, 130(9):989-993.
[24] Kiesslich R, Holfelder M, Will D, et al. Interventional ERCP in patients with cholestasis. Degree of biliary bacterial coloniza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J]. Z Gastroenterol, 2001, 39(12):985-992.
[25] Mukaiya M, Hirata K, Katsuramaki T, et al. Isolated bacteria and susceptibilities to antimicrobial agents in biliary infections[J]. Hepatogastroenterology, 2005, 52(63):686-690.
[26] De Waele B, Van Nieuwenhove Y, Lauwers S, et al. Biliary tract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J]. Surg Infect(Larchmt), 2003, 4(3):241-246.
[27] 郑惊雷, 梁力建, 赖佳明. 胆道感染病原菌及其对抗生素敏感性变化的研究[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5, 25(2):86-88.
[28] 陈国忠, 沙青, 褚爱春, 等. 胆道感染病原菌谱及其耐药性[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3, 13(7):686-688.
[29] Westphal JF, Brogard JM, Caro-Sampara F, et al. Assessment of biliary excretion of piperacillin-tazobactam in humans[J].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1997, 41(8):1636-1640.
[30] Muder RR, Agarwala S, Mirani A, et al. Pharmacokinetics of cefoperazone and sulbactam in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J]. J Clin Pharmacol, 2002, 42(6):644-650.
[31] 张玉, 王凯平, 潭红艾, 等. 胆道手术病人中头孢曲松钠的药动学[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01, 21:537-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