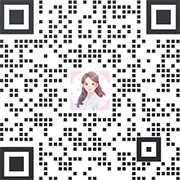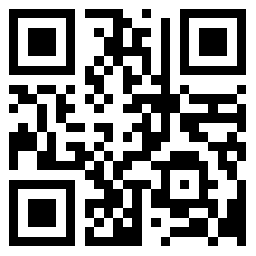脑的神经再生
发表时间:2011-06-15 浏览次数:669次
作者:刘勇,刘建新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研究所,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侧脑室室管膜下区和齿状回的颗粒下区的神经祖细胞通过增殖和分化产生新生细胞的神经再生过程终生存在于哺乳动物脑内。本文综述了神经祖细胞增殖、迁移、分化并功能性整合的调节机制,并对病理条件下的神经再生以及脑内神经再生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希望对神经系统疾病的替代治疗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神经再生,神经干细胞,神经祖细胞,室管膜下区,齿状回颗粒下层
Neurogenesis in the brain
LIU Yong, LIU Jianxin
Institute of Neurobiology, Medical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Neurogenesis is sustained throughout adulthood in the mammalian brain due to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adult neural progenitor cells found in the subventricular zone of the lateral ventricles and subgranular zone of the dentate gyrus. This review covers recent findings that elucidate different aspects of regulation of neurogenesis, including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to mature neurons and functional integration into the existing neural circuits. Furthermore, this review also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on adult neurogenesis in both rodent models and human patients as well as some of the potential problems or limitations in neurogenesis research, which may shed some light on developing novel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replacement treatment of neurological disorders.
KEY WORDS: neurogenesis; neural stem cell; neural progenitor cell; subventricular zone; subgranular zone of the dentate gyrus
在成年哺乳动物大脑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新神经元产生。这些新生神经元分别来自脑内两个狭小的区域:侧脑室的室管膜下区(subventricular zone of the lateral ventricles, SVZ)和海马齿状回颗粒下区(subgranular zone of the dentate gyrus, SGZ)(图1)。来自SVZ的新生神经细胞通过长距离的迁徙到达嗅球,成为那里的中间神经元;来自SGZ的细胞则到达临近的齿状回颗粒细胞层,成为那里的兴奋性神经元。上述现象在哺乳动物脑内终生存在,神经科学研究者称之为脑的神经再生(neurogenesis),而这些寄居于SVZ和SGZ、具有一定增殖分化潜能的细胞就是脑内的神经祖细胞(neural progenitor cell, NPS)。它们之所以没有被明确称为神经干细胞(neural stem cells, NSCs),是由于它们在体外培养时所具有的自我更新特征和可以分化为所有类型神经细胞,即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的能力并没有从体内得以证实。因此,在这里我们用“神经祖细胞”来总体地描述脑内所有可分裂并具有一定分化能力的细胞。
那么,在大脑的其他区域是否也存在神经再生现象?研究者普遍认为,即使在大脑灰质、脑室的其他部位存在NPS,但由于它们的增殖过于缓慢,也很难被观察到或者加以利用。研究已证实,在脑内广泛存在胶质祖细胞(glial progenitors),但这些细胞在体内并不能分化成为中枢神经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单位--神经元[1]。
脑内存在可增殖细胞库和神经再生现象使科学家、甚至公众看到了新的希望:是否可以通过操纵内源性神经再生对许多疾病造成的神经组织损伤起到神经元替代和功能修复作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们正在对脑内NPS的生物学特征、神经再生的调控机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疾病治疗进行夜以继日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进展。
1 脑内NPS的生存微环境和生物学特征
研究者认为,微环境因素可能为NPS的增殖、分化、存活、迁移并进行功能整合提供保障,这种微环境被称作为“神经发生微环境(neurogenic niche)”。在SVZ周围,室管膜细胞表达Noggin蛋白可以通过阻断骨形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 BMPs)信号途径促进SVZ的神经再生[2],室管膜细胞还可能通过色素上皮源性因子(pigment epitheliumderived factor)促进SVZ的NPS自我更新[3]。另外,多巴胺能神经末梢也紧临SVZ的NPS,它们可能通过D2样多巴胺受体促进NPS的增殖[4]。SGZ的NPS紧邻致密的齿状回颗粒层,周围成熟和新生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齿状回门区(hilus)的GABA能中间神经元共同参与SGZ的NPS微环境构成。有研究表明,星形胶质细胞可能通过Wnt信号途径调节SGZ的神经再生[5]。另外,脑内NPS的增殖和周围的微血管环境紧密相关,从脑内微血管释放出的一些因子可能直接作用于NPS。
啮齿动物脑内的NPS表达Nestin、GFAP、GLAST和Sox2等标记物,但这些标记物并非NPS所独有。表达这些标记物的细胞是否一定就是NPS,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
SVZ存在有3种类型的NPS。B型为GFAP阳性的NPS,C型为运输扩增细胞,A型为迁移成神经细胞。其中B型细胞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区分3种类型的细胞主要依靠电镜下的形态学分析,C型和A型细胞还可以通过BrdU、DCX和聚唾液酸神经细胞粘附分子(polysialic acidcontaining neur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PSANCAM)等特异性标记物标记来区分。SVZ的NPS分化潜能是有限的,其后代的命运已经被从神经系统早期发育阶段所得到的生物信息所决定[6]。在正常啮齿动物的大脑,SVZ的细胞与沿着局部血管延伸的基膜相互作用,新生细胞通过RMS(rostral migratory stream)链式迁移路径到达嗅球,并开始放射状的向颗粒细胞层和球旁细胞层迁移[7]。经历形态和功能演变的新生神经元形成功能性GABA受体并最终整合为颗粒神经元和球旁神经元。整个过程大约需要数周时间去完成。这种链式迁移形成一个延伸的细胞聚集带,并被星形胶质细胞所包绕。虽然这些星形胶质细胞在细胞的迁移中并不起关键作用,但它们可能通过调节GABA的水平而影响细胞迁移速度。SVZ三型NPS的功能意义仍不清楚,一些研究者认为它们似乎只是处于不同分化阶段的NPS。
根据形态学和表达的生物标记物不同,SGZ的NPS分为Ⅰ型和Ⅱ型。Ⅰ型海马NPS具有长的放射状的突起跨越颗粒细胞层,到达齿状回分子内层,这些细胞表达Nestin、GFAP和SRY蛋白相关的含HMG box的转录因子Sox2等。Ⅱ型海马祖细胞的突起很短,而且不表达GFAP。SUH等[8]新近的研究表明,表达Sox2的海马NPS具有自我更新能力,不仅可以分化成为神经元,还可以分化成星形胶质细胞。首次表明海马的NPS具有NSCs的特征。SGZ的新生细胞通过短距离的迁移达到齿状回的颗粒细胞层。新生的颗粒细胞在GABA的作用下发生去极化和超级化,这对于它们的成熟至关重要。新生细胞在2周时与门区的细胞和CA3区的锥体细胞开始形成突触,在2~4周时开始长出树突棘。大约在第4周,新生细胞已经展现出了成熟颗粒细胞的特征,但实际上,它们的形态和功能变化仍在继续。新生颗粒细胞一旦成熟,它们就像齿状回的其他神经元一样开始接受谷氨酸能和GABA能神经元的投射[910]。
很多新生神经元在它们产生后的4周内死亡。有多种机制参与调节这些新生细胞的存活。事实上,新生神经元是否能够生存和整合,在它们产生后的1~3周内已经被大致确定。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海马新生未成熟神经元和不同形式的学习记忆形成有关。总之,脑内神经再生是经过细胞增殖、早期分化、存活、迁移、终末分化和功能整合等一系列事件,而完成由NPS成为脑局部成熟神经元的过程(图2)。
2 脑内神经再生的调控
脑内神经再生的调控是一个包括细胞外因素和细胞内机制的复杂过程,它是神经再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2. 1 细胞增殖的调节
2.1.1 生长因子
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 FGF2)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体外培养NSCs的增殖。在体内,EGF和FGF2也可以促进SVZ和SGZ的细胞增殖并维持脑内的可增殖细胞库。不仅外源性生长因子有这样的作用,内源性EGF和FGF2对于体外培养和体内NSCs/NPC增殖也是非常重要的[11]。事实上,EGF受体主要表达于介于NSCs和神经前体细胞之间的NPS。转化生长因子α(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α, TGFα)通过SHH(sonic hedgehog)信号途径调节成体脑的神经再生[1213]。另外,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14]、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IGF1)[15]等都是调节脑内细胞增殖的重要因素。
这些生长因子除了可能直接作用于NPS外,也可能作用于其他类型细胞,通过改变NPS的微环境而调节神经再生。学习、锻炼和环境改善对神经再生的促进作用就可能是通过对上述生长因子的调节而实现的。另外,FGF2和TGFα都产生于星形胶质细胞,提示通过胶质细胞途径可能会找到调节它们的途径。
2.1.2 神经递质
脑内神经递质已被明确证实参与脑内的神经再生。内源性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可以促进SVZ和SGZ的神经再生[16]。研究表明,上述作用部分是由5HT1a受体所介导的[17],刺激BDNF的表达也是其作用机制之一[18]。另外,5HT能神经在SVZ的带状神经支配可能参与建立NPS的微环境。新近的研究表明,黑质纹状体的多巴胺能系统主要通过其D2受体家族促进SVZ的神经再生[4,19]。还有研究表明,激活D3受体家族也促进了SVZ的神经再生[20],但这种作用具有种属特异性。从蓝斑向齿状回投射的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纤维参与调节海马的神经再生[21]。来自于基底前脑的乙酰胆碱可能通过β2烟碱受体促进齿状回的细胞增殖[2223],SVZ和临近的纹状体内已经被证实存在高水平的乙酰胆碱,提示乙酰胆碱也可能在SVZ的神经再生中发挥作用,但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加以证实。
截至目前,形态学研究没有发现NMDA受体NR1亚基在脑内增殖细胞中的表达,而且,海马的NPS是否表达功能性的NMDA受体也未明确。但海马的细胞增殖却与脑内整体的NMDA受体依赖活动紧密相关。也有研究表明,NMDA受体可以改变脑内神经再生[2425]。GABA可以直接去极化海马Ⅱ型NPS而增加Ca2+内流和神经分化因子NeuroD的表达,提示GABA能神经元的投射可能促进海马Ⅱ型NPS的分化[26]。
我们发现,体外培养的胚胎大鼠神经干细胞表达代谢型谷氨酸受体(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s, mGluRs)的一些亚型,它们是mGluR3、mGluR4、mGluR5、mGluR6和mGluR7,激活这些受体可以明显促进NSCs的增殖;激活mGluR7可以促进NSCs增殖和向神经元的分化,而且,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MAPK途径实现的。
由于这些神经递质的受体在NPS的表达还远未明确,因此它们是否直接作用于脑内的NPS还不能确定。
2.1.3 激素
激素及其分泌的昼夜节律在维持脑内细胞增殖中起到重要作用。IGF1促进SGZ细胞增殖的作用可能是通过雌激素介导的[27];甲状腺素通过α受体促进成体脑内齿状回的细胞增殖[28];催乳素和TGFα共同促进SVZ的细胞增殖和分化[29]。有研究表明,肾上腺皮质激素对于SGZ的神经再生有两方面的作用:绝对水平的糖皮质激素压制神经再生,而完整的激素分泌日夜节律对于糖皮质激素的下游调节子5HT和NO调节神经再生的作用则是必需的[3031]。
2.1.4 神经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也会影响脑内的神经再生。睫状节神经营养因子(ciliary neurotrophic factor, CNTF)通过诱导Notch 1促进培养神经前体细胞的增殖[32]。阻断CNTF降低了SVZ的神经再生,表明它是一个内源性神经再生调节因子[33]。IL6在星形胶质细胞的过表达减少了NPS的增殖[34],这可能是炎症降低神经再生的原因之一。另外,白血病抑制因子(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也可以促进嗅球的神经再生[35]。
2.2 细胞单向迁移的调节
SVZ的新生细胞沿着RMS路径向嗅球迁移,以及SGZ的新生细胞短距离向齿状回颗粒细胞层的迁移是一系列可扩散的化学趋化物、排斥物和局部引导分子协同作用的结果[3639]。趋化因子(chemokines)在定向迁移中起重要的趋化作用,SDF1和其受体CXCR4是参与其中的重要分子。嗅球释放趋化因子Prokineticin 2来引导RMS路径上的成神经细胞[40]。相反,在迁移细胞的尾部,由隔核和脉络丛分泌的神经迁移导向因子slit蛋白则起到排斥的作用[4142]。
在细胞的迁移过程中,保持迁移细胞粘聚在狭窄的迁移路径无疑是重要的。由围绕RMS的胶质细胞管表达分泌的粘蛋白tenascinC的排斥作用可以使迁移的新生细胞聚集在一起[4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分子也可能参与迁移细胞之间的粘附。有研究表明,Eph/ephrin信号途径在维持迁移链的粘聚中起作用[44]。
细胞外基质在引导细胞迁移中起到关键作用。α6β1整联蛋白和与整联蛋白结合的细胞外基质蛋白,如层粘连蛋白(laminins),便是发挥这种引导作用的重要分子[4547]。表达于RMS和周边的Neu基因调节剂neuregulins可能通过ErbB4促进成神经细胞的粘附性迁移并引导迁移细胞达到嗅球的颗粒细胞层和球旁细胞层[48]。另外,RMS链式迁移也依赖于迁移细胞表达的PSANCAM[4951]。
在RMS的终点,迁移细胞就会呈辐射状地到达最终目的地。这一过程是由颗粒细胞和嗅球的内丛状层分泌的粘蛋白tenascinR[52]以及僧帽层分泌的reelin[53]所调节的。TenascinR、reelin和促红细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等也在引导迁移细胞转向需要细胞替代的区域中起作用。
2.3 细胞分化和整合的调节
虽然新生神经元可以整合到局部神经网络并成为功能性神经元,但目前对于调节新生细胞表型分化的机制还远未明确。比如,到达嗅球的迁移细胞分化成为GABA能和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比例为9∶1,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
在体外,BDNF促进胚胎或神经前体细胞向GABA能神经元分化[54]。研究表明,在SVZ联合应用骨形态发生蛋白抑制剂noggin和BDNF导致在新纹状体形成新的GABA能神经元并发出轴突投射到临近的苍白球[55]。
维甲酸(retinoic acid)诱导新生细胞向神经元分化,并且和生长因子或低氧条件一起促进新生细胞分化成为多巴胺能神经元[5657]。有研究表明,RMS迁移路径中转录因子Pax6可能参与细胞向多巴胺能神经元转化的调节机制[58]。
除了生长因子、神经营养因子、神经递质等介导的经典信号途径外,还有一些胞内机制被证实参与NPS的行为调控[59]。例如核受体TLX、Bmi1等转录因子参与生后NSC的维护,转录因子Pax6促进SVZ的NPS分化。缺乏甲基化的CG序列结合蛋白1(methylCpG binding protein 1, MBD1)可导致NPS基因组稳定性的破坏和细胞分化的抑制。另外,和细胞周期调节、DNA修复以及染色体稳定有关的基因都参与成体脑内神经干细胞功能的维护和支持。
3 神经再生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脑内神经再生的生理意义尚未阐明。SVZ的神经再生在嗅觉的学习记忆中起到重要作用,SVZ神经再生的减少会导致气味辨别和气味记忆障碍,但二者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有待确定[7,60]。虽然一些研究表明SGZ的神经再生在认知功能中的潜在作用,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否定的结论[59]。
中枢神经系统的很多疾病都会影响SVZ和SGZ的神经再生,但其病理生理意义尚不清楚。癫痫发作可以加剧SGZ的神经再生[61],新生细胞可以功能性地整合在海马的神经网络中,但却形成了病理性的联结[62]。一些抗癫痫药物可以抑制癫痫发作诱发的神经再生。
啮齿类动物局灶性或全脑缺血均可导致SVZ和SGZ的神经再生[63]。我们运用DiI标记室管膜/室下区细胞,采用累积式的BrdU标记方法标记新生细胞并通过双重免疫荧光染色确定细胞分化,发现局灶性脑缺血后,室管膜、室下区细胞迁移到梗塞区周围并分化成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脑缺血后SVZ附近nNOS的减少可能是促进神经细胞再生的机制之一[64]。我们还发现,NPC在永久性脑缺血后沿胼胝体腹侧向缺血方向迁移,而且bFGF是其存活、增殖和分化的有效丝裂原[65]。
缺血损伤组织释放的各种因子有些是促进神经再生的,有些却对神经再生起到抑制作用,而且这些因子之间也相互作用。脑缺血损伤后新生细胞可以在血管的引导下到达缺血区的边缘并开始表达局部神经元的标记物。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风患者。因此,脑缺血后对神经再生的刺激被认为是脑内的修复现象。但这些新生神经元能在局部存活多长时间,并在多大程度上整合入局部的神经网络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许多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也会影响脑内的神经再生。对于Alzheimers病模型动物神经再生变化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66]。在过表达突触前神经末梢膜蛋白αsynuclein的Parkinsons病模型动物,SVZ和SGZ细胞增殖虽然没有显著变化,但新生神经元的存活率却明显降低。Alzheimers患者SGZ[66]、Huntingtons患者SVZ[67]的细胞增殖增加,而在Parkinsons患者,SVZ和SGZ的细胞增殖却明显下降[68]。
炎症反应降低了脑内的神经再生[69],这种现象也可以被抗炎药物所逆转。脑内反应性胶质细胞增生也阻碍脑内的神经再生。但也有研究表明,不同病理条件下的炎症反应对神经再生的影响也可能是不同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疾病,如HIV感染[70]和药物成瘾[71],也影响成体脑的神经再生。神经再生还和抑郁症有关。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压制了SGZ的神经再生,SGZ神经再生的减少也会降低抗抑郁药物治疗的行为学效果[7273]。
上述疾病可以明显影响脑内神经再生以及疾病的病理改变和神经再生的明确相关性,清楚地表明,内源性神经再生具有修复脑病理损伤的潜能。目前,神经再生的调节理论已被逐渐应用于药理学研究,希望通过药物干涉促进疾病后的神经再生、进行损伤神经元的替代,并缓解疾病的症状。也有一些动物研究通过使用神经递质激动剂、生长因子等达到了部分症状缓解目的。我们在对很多相关中药进行的研究筛选后,发现川芎嗪可以显著促进大鼠脑缺血后SGZ、SVZ及皮层内神经干细胞增殖,研究结果还提示抑制nNOS的表达可能是其实现促神经细胞再生的作用的机制之一[7475]。
但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通过干涉神经再生而达到上述疾病的治疗目的还存在诸多问题:①通过药物刺激神经再生是否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尚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癫痫后增加的海马神经再生有助于苔藓纤维芽发等病理性兴奋性神经环路的形成,从而加剧慢性癫痫病理基础的形成。②药物对疾病后神经再生促进作用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动物模型水平,它们对人类疾病患者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资料。③动物实验中,通过口服神经递质激动剂或者局部直接注射生长因子可以促进脑内神经再生,但人类大脑内细胞增殖率远低于啮齿类动物,因此药物干涉能否调集足够的新生神经元而达到替代修复的作用也是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④从理论上讲,通过刺激细胞增殖并应用化学趋化物可以引导新生细胞到达新纹状体等Parkinson疾病相关脑区,但目前还不能控制这些新生细胞定向分化成为多巴胺能神经元。⑤人脑SVZ到豆状核、纹状体或缺血区的解剖距离较大鼠等啮齿类动物远得多,要使新生细胞定向迁移到这些脑区,需要在刺激细胞增殖的同时应用化学趋化物和引导物,这样的手段能否在患者的病理脑区产生足够的功能性神经元尚需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够证实。⑥调节因子的副作用和药代学问题。比如,虽然生长因子加强细胞增殖的效果很明确,但由于生长因子也可刺激错误的细胞,从而会出现身体其他部位的副作用。另外,绝大多数生长因子不能穿透血脑屏障,使药物的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⑦尤其重要的是,药物刺激的神经再生能否使新生细胞在病灶局部达到功能性整合可能是目前及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难题。
4 脑内神经再生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已经使人们对成体神经再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研究者已经确信神经再生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认识到从细胞增殖到新生神经元的功能性整合的再生过程受到了复杂的细胞内机制和外源因素的调控和影响;初步表明了脑内神经再生的行为学功能和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联系。
脑内神经再生的研究不仅可能开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自身替代修复治疗的新前景,也可为细胞移植治疗提供细胞行为调控的手段,并可能会给其他干细胞甚至肿瘤干细胞的生物特征研究提供线索和依据。因为发生在不同脑区、不同微环境的神经再生和胚胎期和生后的神经再生,与其他干细胞包括肿瘤干细胞的病理行为存在一些共同的调节因子和相似的调节机制。但目前,脑内神经再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许多重大甚至基本的理论问题亟待解决:①脑内是否存在真正“神经干细胞”?一般来讲,NSCs主要指在组织培养中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分化潜能的细胞,而这些特征在脑内的可增殖细胞中并没有展现出来。脑内有没有NSCs,如何去鉴定和分离它们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②“niche”,既微环境,是体内神经干(祖)细胞研究的重要理论。那么在“niche”中到底存在怎样的细胞和分子成分?它们和神经干(祖)细胞之间如何作用?③目前对于细胞增殖、分化、存活、成熟和整合调控的分子机制还尚待进一步阐明。许多有关神经再生调节机制的研究都是通过静脉注射某些调节因子或敲除目标基因进行的,我们不能排除它们对神经再生的影响可能只是这些调节因子的间接作用或基因缺失后早期发育障碍的结果。因此,为了精确阐明神经再生调节的分子机制,对目标分子采用更为特异的研究手段是必须的。④虽有研究试图揭示SVZ和海马神经再生的功能,但它们在嗅觉记忆、认知功能或情感行为中的确切作用尚不得而知。弄清楚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深入了解嗅球和海马的高级功能,而且有助于发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新方法和新策略。
我们相信,通过神经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不懈努力,通过药物或其他手段调控脑内的神经再生并使其达到脑损伤替代修复治疗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