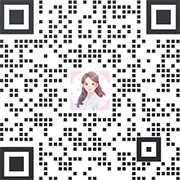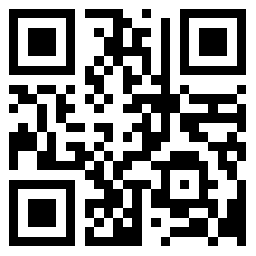《普济本事方》杂病证治的学术思想探析
发表时间:2014-04-24 浏览次数:1583次
许叔微,字知可,宋代真州白沙(今江苏仪征)人,约生于公元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卒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绍兴二年曾举进士,任徽州、杭州教官及翰林集贤院学士,故后世多以“许学士”称之。他不仅是宋代研究伤寒的著名医家,而且在杂病证治方面也多有建树。所著《普济本事方》(以下简称《本事方》)十卷中,有六卷专述杂病证治,涉及中风、痹症、头痛头晕、痰饮、咳嗽、消渴、血证等多种病症,先述方名、主治,次列具体药物和制法、服用剂量及验案,简明切要,语无泛谈,对后世影响较大。特就其杂病治疗及遣方用药方面的经验进行整理、探讨如下。
一、调治杂病,重视脾肾
许氏调治杂病,重视脏腑辨证。脏腑之中,尤重脾肾。他在《本事方·伤寒时疫》及《伤寒百证歌·伤寒脉证`总论歌》等篇中反复指出:“跌阳胃脉定生死,太溪肾脉为根蒂。”[1]6“定生死”“为根蒂”,既反映了脾胃乃人体生死之所系,肾为一身精气之根本的观点,又提示脾肾两脏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关键地位。关于脾胃,他认为“脾为中州土,主四肢一身之事Ⅱ1J94。并在《普济本事方续集》云:“何谓须用胃气,缘胃受谷气,谷气生则能生气血,气血壮则荣卫不衰,荣卫不衰则病自去矣。五脏六腑表里之间,皆出自谷气而相传授,生气血而灌荫五脏。”[2]1视脾胃为维持全身脏腑气血正常生理功能之根本所在,故而把健补脾胃之气作为调治疾病的大法。在辨治饮证、腹胀、水肿、泄泻、消渴、虚热等杂病以及瘥后调理方面,许氏灵活把调补脾胃的方法运用于上述疾病的治疗。如许氏自制的“人参丸”(人参、山萸肉、白术、白茯苓、石斛、黄芪、五味子)“平补五脏虚羸,六腑怯弱”[3∶32,以收健脾益气之功效;治虚损的“加料十全饮”“妙香散”[1]122,皆以健补元气为主;治疗食欲不佳,纳呆的“七珍散”(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黄芪、山药、粟米)[3123具有开胃、养气进食的功效;治胃热呕吐的“竹茹汤”(干葛、甘草,半夏、姜汁、生姜、竹茹、枣)[3]5:清热养阴、和胃降逆;治“月卑元久虚,不进饮食,停饮胁痛”的安神镇心曲术丸(神曲、白术、干姜、官桂、吴茱萸、川椒)温阳散寒,行气化湿;白术汤(白术、厚朴、桂心、桔梗、干姜、人参、当归、茯苓、甘草)温中健脾,治寒气停聚、胃气失展;名方“实脾散”温脾阳,利水湿,治脾虚浮肿等。由上可见,许氏调治杂病,时刻把“调护脾胃,促进饮食而全谷气”作为治疗杂病的根本所在。许氏常用的调补脾胃药物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黄芪、山药等。
许氏认为肾乃一身之根蒂,先天之化源,气血的生化及新陈代谢的进行都离不开肾及肾中真火的作用。故曰:“若腰肾气盛,是为真火,上蒸脾胃,变化饮食,分流水谷,从二阴出,精气人骨髓,合荣卫行血脉,营养一身,其次以为脂膏,其次以为血肉也,其余则为小便。”[I]122《本事方·卷六》论述“小便数”的病机是“腰肾既虚冷,而不能蒸于谷气,则尽下为小便,故味甘不变其色,清冷则肌肤枯槁也”[3]94。又指出消渴病的根源为肾火虚衰,“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若以板覆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能上,此板则终不得润也。”[3]94深入阐述了肾主水、肾藏精和肾中阳气的蒸腾、气化作用以及消渴病的发病机制。许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补脾不若补肾”之说,但他重视肾及肾中真火的思想显而易见,也给严用和提出“补脾不若补肾”理论以极大启示。
在补肾用药方面,许氏根据《内经》“肾主水,恶燥”之论,主张补肾宜用润剂,认为附子、硫黄、钟乳、练丹之类刚燥之剂,用之虽可温助阳气,但无益于补肾。并以仲景八味丸示例,指出此方虽补阳气,但药用地黄,意在滋润,使精中生气。因此,许氏在治疗中风偏瘫、消渴、虚劳、肾脏风及足膝腰腿脚气等杂病方面,重视益肾,但用药力戒刚燥而主温润。如治疗肝肾亏损、腰膝疼痛的“思仙续断丸”[3]71来“益精凉血,坚强筋骨,益智、轻身耐老”;治疗风湿腰膝疼痛的“地黄丸”[3]70具有“益气血、补肝肾、祛风湿、壮腰膝”的作用;治疗虚热用“生地黄煎”等。调肾善以地黄为主,常配伍鹿茸、苁蓉、山萸、菟丝子等,取其滋润摄精、血肉填精之用。其常用的温润药可分两种:一为草木之味,如地黄、肉苁蓉、补骨脂、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巴戟天、山萸肉、杜仲、川断、五味子、茴香、胡桃等;二是血肉有情之品,如鹿茸、鹿角胶、羊肾等。许氏创制的温润滋养法,对后世温肾治虚用药有一定的启迪。张景岳治疗命门水火亏虚之证,以填补真阴,滋养精血为大法,尤以擅长运用熟地而著;口十天士善用血肉填下,温通任督,均得力于许叔微的影响。
二、杂病顽症,善用虫蚁搜剔通络
治疗积聚、痹证、疼痛等疑难杂病以及惊厥等神志疾患时,许氏重视搜剔祛邪,善用具有攻逐走窜、通经达络、搜剔疏利的虫类药物。如“治白虎历节,诸风疼痛,游走不定,状如虫噬,昼静夜剧,及一切手足不测疼痛”[3]剞的麝香丸,方由川乌、全蝎、地龙、麝香、黑豆组成,方中重用生全蝎达21只,生地龙半两,搜风通络,散寒镇痛;治疗胁肋疼痛的神保圆,方由木香、胡椒、干蝎、巴豆组成,其中重用干蝎10只,伍以理气导滞之品通络止疼;治疗偏头痛的白附子散[3]37,方中以白附子、麻黄、川乌、干姜祛风散寒,南星、全蝎、麝香通络止痛,朱砂镇惊。又如治疗“惊忧积气、心受风邪、牙关紧急、涎潮昏塞”[3]21的惊气圆,方中以白僵蚕、花蛇搜剔通络,伍以天麻、朱砂、天南星、木香等化痰镇静开窍。其治疗小儿风厥一证的蝎蛸丸更是集全蝎、白附子、硫黄于一方,用于“吐利生风,昏困嗜卧,或时潮搐”,疗效甚佳。他在《本事方·卷三·积聚凝滞五·噎膈气》中总结通络类药物功效时曰:“抵治积,或以所恶者攻之,以所喜者诱之,则易愈⋯⋯水蛭虻虫治血积,木香槟榔治气积,牵牛、甘遂治水积⋯⋯各从其类也。”[3]49这里不仅指出虫类药中的水蛭、虻虫善治血积、是治血积之首选药物,而且进一步指出虫类药物应用时,要“用群队之药”,若“分其势则难取效”[3]49确为经验之谈。清代叶天士“久病入络”理论的提出,大都是汲取许氏的思想和观点发展而成的。叶氏除继承了许氏虫类药物搜剔通络的经验外,还在仲景《金匮要略》用“旋覆花汤”通络的启示下,发展了通络的方法。把辛润、辛香、辛燥等通络方法广泛用于杂病的治疗中。因此,《本事方》被叶天士视同“枕中秘”。当代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在治疗风湿病、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疑难重症方面善于使用虫类药物,认为使用得当,会取得比传统植物药更加显著的效果[4]208。因此,许氏使用虫类药的经验弥足珍贵,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继承。
三、善用古方,灵活化裁
《本事方》一书共载方370余首,所列方剂均标明出处,其中治疗杂病的大部分方剂出自于《千金方》《和剂局方》《必用方》《活人书》《千金髓》《经效产宝》等医书,另一部分方剂则来源于庞安时、孙兆、杨吉老、沈括、医官都君予、张医博士、蔡太师、张昌时、晁推官、郑康德、崔元亮、田滋、大智禅师、佛智和尚、湛新道人的经验方、民间的单验方以及家藏秘方。这些方剂不是比他药捷而效速,就是有饮食倍进、饮啖如故,终剂而愈或数服即愈的效果,值得临床应用参考。例如治疗破伤风的名方——玉真散,虽然早在唐代已有临床应用的类似记载,但其方名却首见于许氏的《普济本事方》。因此,许氏在保存和继承前人有价值的经验方面,给后世治疗杂病留下了弥为珍贵的史料。除善于汲取和传承前人的经验外,许氏在调治杂病方面也非常很重视对古方、经方的化裁和应用。如许氏治疗肝虚受风、定魂挟正的真珠丸[3]1系在《金匮要略》酸枣仁汤基础上,加入真珠母、龙齿二味直人肝经以镇飞扬浮越之神魂,配伍人参、柏子仁、当归、地黄培土荣木、补血养肝;犀角凉血清火以除烦,沉香行气不伤气,温中不助火,扶脾达肾,引火归源,从而熔定魂与补虚于一炉,发展了前人理论,并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故清末名医张山雷在《中风斟诠》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近世平肝熄风之法,知有珍珠母者,实自叔微此方(即真珠丸)开其端。”治疗自汗恶风的防风汤(白术、防风、牡蛎)则为玉屏风散之变法,方中以味咸收敛之牡蛎代黄芪,配伍甘温之白术健脾益气,辛温之防风以发散,增强了敛汗固表的功用。在甘温、辛温药物基础上配伍咸味收敛之品的用药经验,显然是许氏对前人经验的发展。对此,清代俞震在《古今医案按·伤寒》按中曾赞其曰:“仲景《伤寒论》犹儒书之《大学》《中庸》也。文词古奥,理法精深,自晋迄今,善用其书者,惟许学士叔微一人而已。所存医案数十条,皆有发明,可为后学楷模。”除化裁古方外,许氏又长于创制新方,以广临床应用。如被后世广泛运用治脾肾虚弱纳差的二神丸、五更泄的四神丸、腹痛泄泻的温脾汤、治疗中风闭证的稀涎散等。清代汪昂《医方集解》收载《本事方》的方剂有八首,如治一切积聚痰饮、心胁引痛的硇砂丸,治肠风脏毒下血的槐花散,治心中烦躁、不生津液、不思饮食的黄芪汤,治产妇老人便秘的麻仁苏子粥,治妊娠中风的羚羊角散等方,这些方剂和经验对后世杂病证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刘景超,李具双. 许叔微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
[2]邹澍撰. 类证普济本事方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许叔微. 普济本事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4]朱良春. 朱良春医集[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