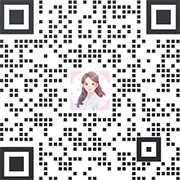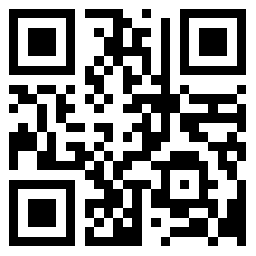D型人格: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心理危险因素
发表时间:2011-07-04 浏览次数:735次
作者:于肖楠 张建新 作者单位: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摘要】 D型人格(又称忧伤人格)是指经历消极情感与社会压抑的混合倾向。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这种心理危险因素与其生活质量下降、梗死复发甚至死亡等有着密切联系。作者总结了D型人格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现状,阐述了D型人格对于识别早期高危患者的临床价值,探讨了神经内分泌学、免疫学及心理学等方面的机制,并评价了对D型人格进行心理干预的可行性。
【关键词】 D型人格 心血管疾病 消极情感 社会压抑 心理干预
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在发达国家中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列为第一位,而近年来我国的心血管疾病比例也呈上升趋势。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简称 CHD)是心血管疾病中最主要的疾病类型[1]。.
研究者在探讨心血管疾病发病、治疗、预后过程中的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的作用时,对患者的心理因素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研究发现,人格特质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70年代的研究曾发现,A型人格[2]、抑郁[3]和敌对[4]等与心血管疾病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然而,这些关于心理机制的研究在经历了多年的热潮以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众多的研究导致了不一致的结论,因此有人断言,在心血管疾病的身心关系研究中,人格概念已经不合适了;但仍有些人坚信,特定的心理特质间的相互作用会比单一变量对健康产生更强的影响。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更高水平的重新整合,身心关系的研究也开始了将这些孤立的、不稳定的人格碎片联合起来的工作,以便构建一种更具整合力的人格结构,从而人格提高对心血管疾病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1 D型人格的概念
荷兰学者Denollet经过实证归纳和理论演绎,于1996年提出了“D型人格”(type D personality)的概念,又称“忧伤人格”(distressed personality)[5]。D型人格的提出既是对以往与疾病相关的A型、B型、C型人格概念的扩展,也是对已有人格和心血管疾病关系研究证据的整合。大量研究结果表明,真正对心脏病起作用的心理因素,可能不单纯是消极情感,而是慢性的心理忧伤。目前国内医学心理学领域尚未引入“D型人格”的概念。本文将系统地介绍有关D型人格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
D型人格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格亚类,是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简称NA)与社会压抑(social inhibition,简称SI)的整合。需要注意的是,NA和SI这两种心理因素必须同时出现,才能给心脏带来破坏作用,任意一个单独因素都不会产生强烈的影响。D型人格中的NA是指人们长期经历消极情感的倾向,他们会体验到愤怒、冲突、沮丧、焦虑等情绪,并且这种倾向往往很稳定,不受时间和情境的影响。高NA的人在大五人格量表(NEO-FFI)中的N因素和埃森克人格问卷(EPQ)的神经质维度上会得高分[6]。他们不仅感受到烦躁、紧张,无缘无故的担心,而且对自我抱有消极观念,往往主诉存在很多身体症状,对负性刺激更敏感。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冲突迭起。对于未患冠心病的人来说,NA与胸痛感有关;而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NA则与其身体症状有关[7]。
D型人格中的SI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压抑自己对情感和行为的表达。因为他们与别人接触时感觉紧张、不安全,便会有意识地维持自我压抑的状态。高SI特质的人在大五人格量表中的E因素和埃森克人格问卷的外向性维度上得低分[6]。他们认为,世界充满了威胁,所以与人交往时极不自如,尽量逃避可能出现的危险,如别人的拒绝和尴尬。他们表面上保持平静,但内心极力控制着自我表达,言谈举止很不自信,在交往中始终与人保持着心理距离。具有高SI特点的人,心脏的不良反应增多、心脏复原能力减弱、心率变化缩小,长此以往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引发冠心病,甚至死亡。[7]
2 D型人格的测量
在D型人格的早期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特质焦虑问卷(Trait Anxiety Inventory)来测量NA,采用社会压抑量表(Social Inhibition Scale)来测量SI。但两个量表合在一起条目过多,给应答者带来了负担。所以,Denollet在1998年建构了更具有针对性的D型人格快速诊断工具,即含有16个项目的D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简称DS16)[8]。该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分别测量NA和SI。为了提高D型人格的效度,Denollet在2000年又将烦躁/紧张(dysphoria/tension)和沉默/退缩(renticence/withdrawal)这两个低级特质引入测量,从而发展出24个项目的D型人格量表(即DS24)[7],但这个量表较少应用。目前最新的测量版本是DS14,对NA和SI的7个条目分别计分,比如:“我经常为琐事而小题大做”,“与人交往时我觉得很拘谨”等。该量表采用“0=不符合”到“4=很符合”的五点记分法,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根据临床效标,DS14将10分作为分界点,即将NA≥10且SI≥10的受测者判断为具有D型人格。根据这一标准,大约20%的正常人群、27% ~ 30%的冠心病病人具有D型人格,而这一比例在高血压病人中达到了50%。
3 D型人格的研究价值
D型人格的研究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冠心病确诊患者中,识别出那些容易发生情绪应激反应和复发心脏病的患者,从而可以提前防范这些危险,保证对患者的软性和硬性医疗指标的控制[9]。一些临床观察发现,在控制了心脏病症状、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如吸烟饮酒)等危险因素以后,D型人格组病人的死亡率仍远高于对照组。他们在心肌梗死后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6倍,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可能性提高4倍。这种人更容易复发心血管疾病,无法坚持治疗。而对于得过心脏病的D型人格患者来说,他们的复发率提高了4倍,得心脏骤停(sudden cardiac arrest)的危险性提高了7倍,而且更容易引发梗死等致命的或其他非致命的心脏病。在治疗过程中,他们的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简称LVEF)也会大幅度下降,需要特殊的护理。另外D型人格也是影响人们情绪和社会健康的重要因素。这类病人多会体验到长期的心理悲痛,缺乏积极情感,自尊心不强,不满于生活现状,生活质量也会下降。并且即便多年以后,D型人格患者的健康状况仍不如对照人群,他们一直抱怨自己胸痛,并长期依赖于镇静药,没有能力重返工作。
4 D型人格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作用机制
鉴于D型人格的研究刚刚兴起,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对人格-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做出充分的解释。从生理学血液循环方面的研究结果来看,D型人格患者的血小板功能障碍、心率变化幅度缩小、心肌突然缺血等都会导致他们心血管疾病的再次发作[5]。而精神神经内分泌学方面的证据指出,在应激状态下,D型人格被试的交感肾上腺系统(sympathetic-adrenal-medullary system,简称SAM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简称HPA轴)发生协同激活,产生强烈的唾液皮质激素反应,这种生理方面的超强反应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直接原因[10]。另外,免疫学方面的研究表明,D型人格能激活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病人的前炎症细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肿瘤坏死因子(tumour necrosis factor)(TNF)-ɑ及其受体,而这种受体本身正是预测慢性心脏病死亡的最准确、最可靠的指标,这种慢性心理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可能就是D型人格患者预后不佳的一个原因[11]。而Denollet却认为,D型人格对心血管疾病起作用的机制,在于负性情感和压抑应对起了中介作用。因为情感的抑制使个体不能成功地适应应激事件,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就会形成长期的应激状态,进而对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造成不利影响[7]。此外,D型人格患者的其他不健康行为方式和心理因素(如自我孤立、缺乏社会支持等),可能也是致病的间接原因。
5 D型人格的心理干预
Friedman在1987年曾说过,“尽管把任何一个心理因素说成是病因,还为时过早,也过于武断,但人格对于健康具有潜在的影响效果是勿庸置疑的。即便暂时无法得出定论,但人们和医生都试图通过改变人格来预防或影响疾病(例如‘不要这么拼命工作’,‘把感情释放出来’,或者参加‘如何改变你的A型人格’的讨论班)。因为有效的心理干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终极目标,在人格与疾病的关系中必须以此作为直接核心”[2]。Pedersen和Denollet也认为,除了医疗干预以外,心理评价和干预可能就是减少病人发病和死亡的唯一有效方式[9]。D型人格的系列研究正是以心理干预作为重点,把主要焦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识别目标人群、制定干预的目标、评估干预的可行性。就目标人群而言,在心理上感觉疲劳、士气消沉、烦躁易怒的人都可以成为干预的对象,D型人格测量对于鉴别这些心脏病高危人群很有帮助。尽管这些人很少感受到情绪上的满足和幸福,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存在着社交困难,并且这种人格特点具有跨时间、跨情境的稳定性,但患者采用独特方式来处理情绪应激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情绪应激状态是无法改善的。常用的行为疗法和心理药物干预对于减轻病人的悲伤沮丧、降低愤怒和敌对、改善社会关系等都有较好的效果,因而能成功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当然对患者进行外科手术和内科调节也有一定帮助。其他的干预研究表明,那些针对A型人格、敌对、焦虑和抑郁的心理干预方法,在治疗后的几年里仍然能够抵制心脏病的复发,尽管目前还没发展出直接针对D型人格的心理干预策略,但这些间接证据预示了改变这种心理危险因素的可能性。
在疗效的个体差异方面,Pedersen和Middel的研究发现,患有缺血性心脏病的D型人格患者接受干预后,精力衰竭感虽然已经明显减少,但仍高出非D型人格的患者的3倍,心绞痛症状也更多[12]。也就是说,虽然通过临床干预(包括心理治疗),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悲伤、身体不适和心绞痛症状,但因为患者在情绪应激的基础水平上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所以探讨各种治疗手段对治疗和预后的不同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6 需要注意的问题
尽管有人讽刺D型人格的概念是“新瓶装旧酒”[13],批评它并没有提供关于人格与健康、心血管疾病之间关系的新知识。但它像A型人格、C型人格一样,在理论内核上避免了整体性人格概念的泛泛之论,力图反映一种不同的行为症状和心理特征,以提供更确切的信息。国内学者对这种观点持不同意见,甚至认为是对人格概念的混淆,这可能是源于不同理论背景下对问题的不同理解。同时在构建上,D型人格避免了测量那些过于宽泛、过难定义的人格或行为特点,而将NA和SI这两个在心理学理论中具有明确概念根基的人格特点加以同质组合,使情感状态与应付方式同时得到了考虑。NA对心血管疾病发作的作用已在以往研究中得到广泛证实,而SI作为一个调节变量使NA的效果大幅度提高(而高NA低SI患者的死亡率与低NA相类似),正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D型人格具有了独特而强大的解释力。
需要注意的是,D型人格旨在揭示正常人格特点对心血管疾病的作用,而不是心理病理学的规律。因为针对冠状动脉性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简称CAD)的研究表明,健康人中表现为D型人格的比例与CAD患者大致相同。同时不能草率地把D型人格称为心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格,因为它不是病因学的危险因素。就CAD而言,D型人格只是CAD确诊患者的一个预警指标,能预测出抑郁、社会疏离、幸福感丧失等以及死亡,并且这种预测作用不受左心室功能紊乱等已知的生物医学因素的影响,也跟病情的严重程度无关[14]。
另外,不能将研究焦点仅仅局限于D型人格本身,孤立地探讨这种人格特征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些研究还表明它可以与敌对、防御等心理社会因素及年龄、左心室射血分数等传统生物医学因素联合起来发挥作用,大幅度地提高心脏病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花费大量的医疗成本才能控制这些危险因素的作用[15],所以还需要建立一个更综合的理论框架来探讨心血管疾病的身心关系。目前最有力的研究框架是生物医学、心理社会学(包括特定的情感状态,全面的人格特质等)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有效结合。
综上所述,尽管D型人格对人格-疾病之间关系的诠释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既没有覆盖所有与健康相关的人格维度,也没有阐述个体因素是如何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疾病的,但将D型人格这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引入我国的人格与健康研究领域,仍将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及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崭新的思路。目前D型人格的作用已经在高血压患者[7]、与冠心病并发的癌症患者[16]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但这种心理因素是否对糖尿病、哮喘、关节炎、溃疡甚至艾滋病等其他疾病也具有危险性还尚待考察。另外这种人格特点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已经在荷兰、比利时、挪威、加拿大、德国、丹麦、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国家中都得到了证实,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国家和文化尚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叶任高主编. 内科学. 第5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0. 271~310
[2] Friedman H S, Booth-Kewley S. The "disease-prone personality": a meta-analytic view of the construc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7, 42(6): 539~555
[3] Carney R M, Freedland K E, Miller G E, Jaffe A S. Depression as a risk factor for cardiac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a review of potential mechanism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2, 53: 897~902
[4] Gallo L C, Smith T W. Patterns of host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conceptualizing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son and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9, 33: 281~310
[5] Denollet J, Sys S U, Stroobant N, Rombouts H, Gillebert T C, Brutsaert D L. Personality as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long-term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Lancet, 1996, 347: 417~421
[6] De-Fruyt F, Denollet J. Type D personality: a Five-Factor Model perspective. Psychology and Health, 2002, 17(5): 671~683
[7] Denollet J. Type D personality: a potential risk factor refined.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0, 49(4): 255~266
[8] Denollet J. Personality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Type-D Scale16 (DS16). Annu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98, 20(3): 209~215
[9] Pedersen S S, Denollet J. Type D personality, cardiac events, and impaired quality of life: a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2003, 10(4): 241~248
[10] Habra M E, Linden W, Anderson J C, Weinberg J. Type D personality is related to cardiovascular and neuroendocrine reactivity to acute stress.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3, 55: 235~245
[11] Denollet J, Conraads V M, Brutsaert D L, De-Clerck L S, Stevens W J, Vrints C J. Cytokines and immune activation in systolic heart failure: the role of Type D personality.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2003, 17(4): 304~309
[12] Pedersen S S, Middel B. Increased vital exhaustion among type-D patients with ischemic heart diseas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1, 51: 443~449
[13] Denollet J, Van Heck G L. Psychological risk factors in heart disease: what type D personality is (not) about.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1, 51(3): 465~468
[14] Pedersen S S, Denollet J. Validity of the type D personality construct in Danish post-MI patients and health control.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2004, 56: 1~8
[15] Denollet J. Vacs J, Brutsacrt D L. Inadequate response to treatment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dverse effects of Type D personality and younger age on 5-year prognosis and quality of life. Circulation, 2000, 102: 630~635
[16] Denollet J. Personality and risk of cancer in men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98, 28(4): 991~995